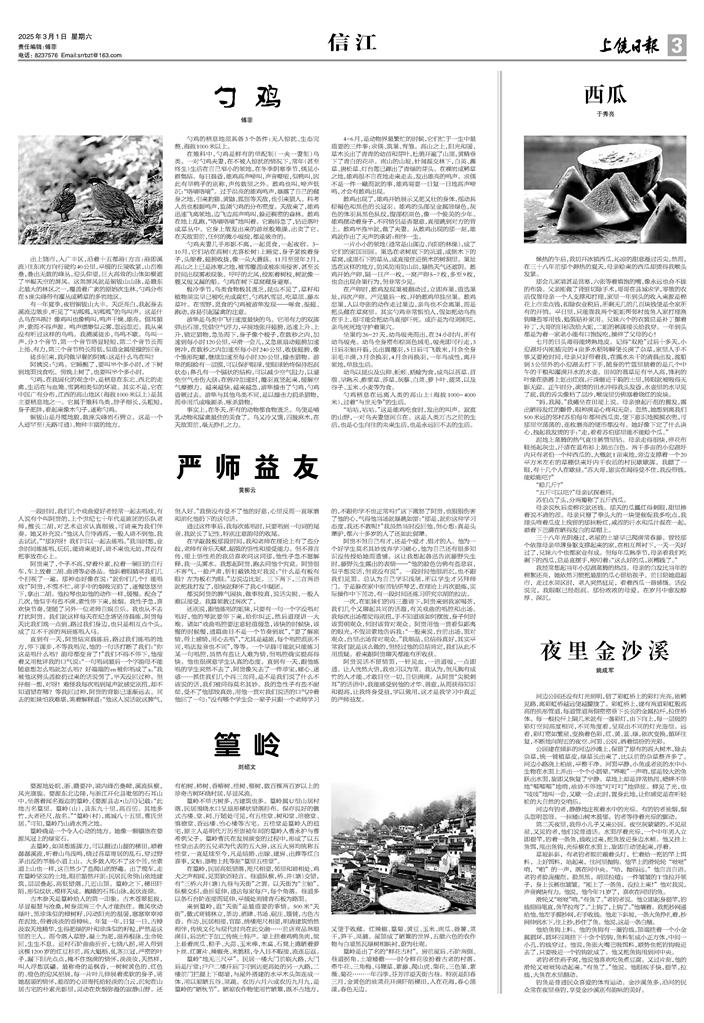于秀亮
燥热的午后,我切开冰镇西瓜,沁凉的甜意漫过舌尖,然而,在三十八年前那个溽热的夏天,母亲赊来的西瓜却烫得我喉头发紧。
那会儿家境甚是贫寒,六张等着填饱的嘴,像永远也合不拢的布袋。父亲刚做了肾脏切除手术,哥哥在县城求学,零散的农活仅靠母亲一个人支撑和打理,家里一年到头的收入来源是棉花上市卖点钱,扣除农业税后,所剩无几的几百块钱便是全家所有的开销。平日里,只能靠我两个姐姐帮邻村放鱼人家打理渔钩赚些零用钱,勉强贴补家用。兄妹六个的衣裳总是补丁摞着补丁,大哥的旧衫改给大姐,二姐的裤脚接长给我穿。一年到头都是为着一家老小能有口饱饭吃,操碎了父母的心!
七月的日头毒得能烤熟地皮。记得“双抢”过后十多天,小迎湖圩内刚插完的4亩多水稻转瞬便长满了杂草,家里人手不够又要抢时间,母亲只好带着我,在露水未干的清晨出发,渡船到3公里外的小迎湖去打下手,随身的竹篮里躺着的是几个中午的干粮和灌满开水的水壶。田间的蒿草足有半人高,锋利的叶缘在胳膊上划出红痕,汗珠砸进干裂的土里,转眼就被吸得无影无踪。正午时分,滚烫的田水冲得我头发昏,水壶里的水早见了底,我的舌尖像粘了层沙,喉咙里仿佛塞着烧红的炭块。
“妈,我渴。”我瘫坐在田埂上说。母亲撩起汗湿的鬓发,露出晒得发红的颧骨,眼神满是心疼和无奈。忽然,她想到离我们500米远的邻村苏伯每年都种西瓜卖,便下意识地摸摸衣兜,可那里空荡荡的,连枚磨亮的硬币都没有。她好像下定了什么决心,拽起我发烫的手:“走,看看苏伯那里能不能赊个瓜。”
泥地上蒸腾的热气直往裤管里钻。母亲走得很快,碎花布鞋扬起灰尘,汗渍在蓝布衫上洇出白色。两千多亩的小迎湖圩内只有老伯一个种西瓜的,大概就1亩来地,旁边支撑着一个20平方米左右的草棚供来圩内干农活的村民歇歇脚。我瞟了一眼,有十几个人在歇昼。“苏大哥,崽实在渴得受不住,我没带钱,能赊账吧?”
“赊几斤?”
“五斤可以吧?”母亲试探着问。
苏伯点了头,分两瓣称了五斤西瓜。
母亲说秋后卖棉花就还钱。那天的瓜瓤红得刺眼,甜里掺着说不清的涩。母亲只掰了拳头大的一块便催促我多吃点,我埋头啃着瓜皮上残留的那抹粉红,咸涩的汗水和瓜汁混在一起,顺着下巴滴在晒得发白的草帽上。
三十八年光阴漫过,老屋的土墙早已爬满常春藤。曾经那个依靠母亲单薄身躯支撑起来的家,在相互帮衬下,一天一天好过了,兄妹六个也都家业有成。但每年瓜熟季节,母亲看我们吃剩下的西瓜,总是直摆手,唠叨着:“这么好的瓜,别糟践了。”
我经常想起当年小迎湖蒸腾的热浪。母亲的白发比当年的棉絮还亮,她依然习惯把最甜的瓜心留给孩子。前日陪她逛超市,走过水果区时,老人突然驻足,看着西瓜一番感慨。话没说完,我眼眶已经湿润。那份浓浓的母爱,在岁月中愈发醇厚、深沉。